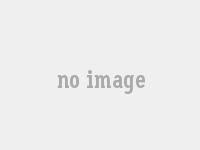
晨哥办公技巧(讨论一下高玉峰 晨哥)
- 办公技巧
- 2023-08-13 13:46:11
- 0
【人物档案】
高玉峰:男。汉族。祖籍山东,生于鞍山。现龄中年,看神气是青年。身高1米8以上,体重200来斤。历任鞍钢工人、团干部、鞍钢展览馆馆长、市科协什么什么主任。1987年入鲁迅美术学院进修,毕业后组建鞍钢摄影家协会任主席。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摄影家协会理事、鞍山市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艺术方面主攻摄影,兼科绘画、美术设计、文艺理论等等。艺术成就小奖不算,大奖拿过辽宁首届摄影金像奖、全国工业摄影艺术联展银奖、中国工业发展四十年摄影联展金奖、中国摄影家突出贡献奖、国际工业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称号),其摄影理论文章散见于全国多家大型报刊。
一个人的形象和条件,往往决定他的职业和命运。“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这说的是外部条件。自身条件,比如獐头鼠目的,上不得台面,只好背地里去经营些什么;面目俊朗的,不拼成个公众人物都对不起祖宗给他的这张脸。其实相面先生都是很唯物的。那么高玉峰呢?相貌堂堂,长发飘飘,还会说山东话,假使戴上戒箍,梳个行者髻,整个一个活武松。尤其是身形壮阔,决定了他只能走两条路,一个是当官,一个是搞艺术。因为你不能想象很有领袖模样的人去做工或去街上摆小摊儿,那肚腩让他的腰弯不下去。
不过高玉峰自己说他年轻时体重才130来斤。这我信,但我想象不出来。我还想象不出,他穿上毛朝外的小大衣(就是裘皮嘛),翻毛的小皮靴子,戴上水獭皮的小高筒帽,是个什么样子?这也是他自己说的,说时很神秘,因为着这份装束时他是个小少爷,鞍山铁西好大一片地界儿都是他们家的工场——“玉东铁工厂”。这样的家世解放后没有受什么打击,一是他父亲救助八路军有功,二是主动接受“三大改造”,积极响应公私合营。但是这样的家世,保证了高玉峰成长为猛男所需的物质条件(大米干饭猪肉炖粉条子随便造),那么对他的精神成长与文化修养,岂能没有意义?要知道,“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的比率实在太小。
家世对高玉峰究竟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猜想。父辈把家业做到那种程度,含辛茹苦不必说,一定还有做人的高度,做事的强度,包括观念、信念、智慧、韬略,等等。高玉峰无缘继承那份家业,可是有缘继承那份创业的精神和理念;新中国断了经营私企的路,他可以用那精神和理念经营自己。开篇档案里已经说了,高玉峰当过官,而且很有步步登高的危险,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艺术。1990年代以来,鞍山市摄影家协会已经换了六任主席,高玉峰一直是常务副主席。就他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艺术水平及社会影响,有关领导和业界同行几次动员他出任主席,他都把大脑袋摇成了拨浪鼓。这我能理解并深有体会,他是不想被事务和俗务缠住天马行空的艺术翅膀。很多人可以做工,可以务农,可以经商,也可以从政,就像麻将里的“混儿”,高玉峰不然。在我看来,高玉峰只能搞艺术,他不仅长的艺术,活的艺术,连头发梢脚趾甲——如果可能的话——都会张扬出艺术来。我意思不是说高玉峰做不成别的,我是说没有比艺术更适合他的了。就他目前活得如斯自在,相信他肯定会同意我的判断。
一点不夸张,高玉峰全身心都活在艺术里。他先前的工作室没有人打扫(当然现在不同了),和垃圾站大有一拼:塞满烟头的烟灰缸、积满茶垢的水杯、挂着五颜六色干的湿的种种毛笔的笔架、卷了边角的各类书籍、杂志堆满了写字台;蒙着灰幕的电脑屏从过期的报纸堆里奋力挣扎出来,还不错,脸蛋子被谁用手掌抹出一片可以观看内存资料的净区,周边灰幕上还留着那勤快的手掌的指印;墙上用图钉横七竖八地钉着放大的摄影作品样片;墙根下堆叠着某次影展的展品;靠墙的几个卷柜门当然是关不上的,各式相机、镜头、胶片盒、三角架与新的、旧的、精装的、简装的摄影集和画集,在柜子里分庭抗礼,挤得柜门呲牙咧嘴;柜子顶上的宣纸画框摞上了天花板,缝隙间居然露出半个佛头和一只陶罐;画架和已成文物的底片放大机、照片裁剪器之类戳在墙旮旯里,趁空儿挂着一两件摄影马甲;调色盘、墨汁瓶、笔洗、圆规、格尺、裁纸刀自然占领了窗台;砚台呢?……“别坐!”高玉峰突然惊喝——砚台正在皮面沙发椅上酣睡,嘴角挂着已经干涸的黑色的哈拉子;这才留神脚下,几幅画完没画完的山水颠三倒四扔在地上,有一幅被踩了一脚,高玉峰捡起来看看:“你别说,这鞋印儿拿笔勾巴勾巴挺像怪石的哈!”……总之,这些无不表明着主人的艺术家风范,甭说别的,瞧人那份……什么,邋遢?不,那叫潇洒!
不过高玉峰把自己拾掇得倒是相当精彩:头发虽长并不蓬乱,衣服上也没有墨水点子颜料斑痕以及浆糊嘎巴。说到衣服,不知从哪儿淘来的,他的着装一年四季总有奇异之处,大红大绿太一般了,只说形制,新潮而又古拙,得体之至貌似订做的。有人赞赏不置,他立刻就要往下脱:“你看好给你!”谁也不能要,要也不能穿,穿也穿不出他那种感觉。
说来有趣,高玉峰自己的工作室不可救药,他却有本事使别人的办公室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我从一篇写他的文章中看到的——顺便说一句,已经有好几位写手拿高玉峰“做文章”了——这篇文章大意是说,一科普部门要办展览,请高玉峰为之策划设计。其间高玉峰来他们办公室,发现好几个人在这一间大屋子里办公,凌凌乱乱,不堪入目。文章的作者发现高玉峰直皱眉,十分窘迫,就办公室的乱象连声抱愧。高玉峰一笑说得啦,我给你规整一下吧。“当我风尘仆仆从俄罗斯回来走进办公室时,不禁被眼前焕然一新的景象惊呆了:首先闯入眼帘的是一盆半人多高的美人蕉,那娇嫩的翠绿给人一种宁静、温馨和舒畅的感觉。偌大的房间已经粉刷一新,光泽亮丽,并被间壁成几个隔断,每个隔断自成一体,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办公桌、书柜和保险箱。隔断呈浅蓝色,仔细一看,是用一种很经济的装饰布做成的。可过去那些破东烂西都哪儿去了?他猜出了我的心思,抬手一指角落里新建的一个小仓库说:喏,都在那里呢。……”写这文章的是一位深爱艺术的单身女性,一位挚诚率真的老大姐。她认为高玉峰是“一个全身心投入艺术的人”,所以“也是个最简单最单纯的人”。对当时同样单身的高玉峰,她早已“僵硬的心”动了。只是因为“他对任何女人都保持着男人的尊严”,而她“心肠是硬的,语言也硬得像石头”,于是,没有情况。
高玉峰是摄影家,这没有疑义。但我要说高玉峰是诗人,恐怕很多人会愣起眉眼:他会写诗吗?就像照相的不一定是摄影家一样,写诗的也不一定是诗人。卓别林不写诗,他的自传题为《一个诗人的梦》,全世界有识之士没人摇头。关于诗的涵义,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认为:“押韵的不一定是诗。分行的不一定是诗。插了诗标的也不一定是诗。诗是一种认知的深度,一种做人的高度,一种灵魂的叹息,一种天籁的低吟,一种哲理的形象之光,一种内省的宗教情结,一种用生命的血泪合着人世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调制而成的百味杂陈的酒;而诗人,应该具有诗化了的心境,诗化了的思维,诗化了的行为。”这需要天资,更需要修化,修化到了骨子里,浑然忘机。高玉峰不承认自己是诗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活得诗意盎然,但他的诗人气象却体现在随便一幅作品中和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里。
其实在高玉峰乱糟糟的工作室里,诗像空气一样简单地存在着。没见过高玉峰刻意地收藏什么,但在这里,废纸篓中都可能躺着个陶甬;用来掭笔的常常是一块瓦当;花草养在不知什么年代的古陶罐里;一块普通的石头上嵌着个树根,盘上去雕成个小达摩;……一切都是那么随意放达,体现着主人飘逸的诗魂与飞扬的真性。在这里,唯一会飞而不能飞的是笼子里那只鸟,但它会说话,不停地叹着气,时而恼怒地喊一声:“老高!”他这儿所以乱也是因为客人太多,来者自然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这里的话题没有张长李短刘是王非,但也很少光圈速度白平衡,更多的是谁的书法怎样,绘画如何,文章深浅,立意高低。话题进入哲学、美学之境,就得听高玉峰一个人白话了。我有一次去凑热闹,来了一位老者,八十多了,来了就坐在一边,不声不响,谁说话他就笑眯眯地看着谁,两个小时后悄悄地走了,正如他悄悄地来。我说老头儿怎么回事?高玉峰说:爱好摄影,总来。可是这里很少有人谈摄影,而且高玉峰每周三次去中老年摄影培训班授课,老头儿干吗要来这儿?我想他完全可能就是要在这种氛围中证明一下自己活着的意义。
或问:这些跟摄影有什么关系?听高玉峰怎么说:“按照古人的观点,人应当遵循‘虚’、‘静’、‘去欲’、‘去己’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人才能实现‘德教行为’、‘知识体系’、‘艺术技能’的目的。因此只有‘虚’才可以接受万物,简单的‘技术’完全不能达到古人说的关于艺术境界的认识。”(高玉峰《浅析摄影美学思想的分化与溯源》)
我问过高玉峰:“现在照相机已经普及到人人会摄影的程度,你们这些摄影家怎么办?”他反问我:“那你说,现在只要会摆弄电脑就能写东西发表,你们这些作家又怎么办?”其实答案已经有了,不用看高玉峰的摄影作品,仅从他的工作室内容,你就知道什么是摄影家与照相的根本区别。
除了理论文章、授课和有关会议,平时高玉峰的确极少甚至不谈摄影,也看不到他长枪短炮左肩右胁地跑来跑去,很多时候他是用别人的相机对突然感兴趣的景致或人物咔嚓几下,说不定就弄出一幅不可复制的杰作。“功夫在诗外”这话早已被人喊滥,但究竟什么是诗外功夫,少有人说得清楚。“各种文化艺术虽然有明显的区别,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都承认环境、教育在人性发展中具有重大作用,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只不过是人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高玉峰《鞍山工业摄影的创作现状与思考》)这说的同样是人所共知的“终身学习”和“终身接受教育”的问题。但是同样,什么事情喊得越热,通常实际上就会越冷。这篇文字所以题为《讨论一下高玉峰》,盖因笔者诚心企望,高玉峰的文化自觉与修为,在当下浮躁的泡沫连天的艺术档口里,能够引起冷静的思考与认同。说到底,他让我坚定了一个认识:如果仅仅醉心于你所喜欢和熟悉的某一门艺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么一个艺术家的路也就到此为止了。很不幸,这样的艺术家比比皆是。
不过高玉峰也不是镇日里满口道学不说“人”话,他的语言系统实际很庞杂。前面提到的那位老大姐,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他阅读广泛,对文学艺术有着独到见解,对尼采、叔本华也很熟悉。他曾走遍大江南北,去过许多国家,所以张口一段故事,闭口一道风情。他讲起故事来不仅绘声绘色,讲到高潮处还会当场来个表演,而且他还有个绝活儿——学啥像啥。”我听过高玉峰学他舅舅。他舅舅在山东,他每年都孝敬舅舅一笔钱。母亲去世时他没有告诉舅舅,舅舅得到消息来了,进了门一脸肃气,一声不吭。高玉峰很紧张,眼珠一转,赔着笑说:“舅,往后一年我给你老再多寄一千块钱!”舅舅这才从鼻子里呼出一口闷气,说话了:“以前俺就跟你表兄弟们说,你是他们的榜样。你要多给俺寄一千块钱,你就是他们的光辉榜样!”
多么动人的款款亲情!但我想说的是,“养儿随娘舅”,这爷俩骨子里都有一种幽默感。幽默不是滑稽,不是耍怪,而是一种高度的智慧。“再没有比懂得幽默更困难的事了。”(米兰·昆德拉《幽默的发明》)高玉峰的智慧很大程度都体现在了幽默上。他可以一本正经地给你讲荒诞不经的故事,也可以漫不经心地和你谈惊天动地的事情。这让我联想他获奖的那几幅摄影作品:极暗的背景下,大工业的机器仅以几束焊火或钢花显现,人物的轮廓也隐进了深邃的想象,而人物脸上的汗滴和嘴巴上的烟头却被赋予了极亮的高光。这种从极暗到极亮的强烈的反差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其冲击力直透骨髓。
还有一种反差:一个两米来高、二百来斤的庞然大物,居然可以吟出如下细巧的句子:
追忆槐花盛开的季节
阳光下一片银色的世界
深深吸一口芳香
悄悄在心房滋长的情思
等待
春风是一把多情的扇
阳光下洒落着槐花雨
遮不住人间的心情
这不是不属于昨天的梦幻
伫立
这是高玉峰的诗。高玉峰还真就会写诗!
2014年8月于鞍山一苇邨
本文由 京廊文化根据互联网搜索查询后整理发布,旨在分享有价值的内容,本站为非营利性网站,不参与任何商业性质行为,文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部分文章如未署名作者来源请联系我们及时备注,感谢您的支持。
本文链接: /bangong/1433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