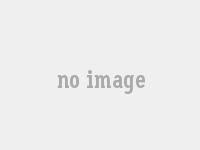
办公技巧组合素描照片写生(基层干部人物素描)
- 办公技巧
- 2023-09-01 04:14:27
- 0
□谢德才
清波
一提起清波,人们就会自觉把记忆往青山绿水中拉,再现细风吹皱的水面。这是美景,固可欣赏。可我说的清波,是个年轻的村官。姓龚,籍贯是浙江宁波。
清波,名字好听。她与宁波一字之差。她也因宁波感到骄傲而自豪。宁波,经济迅速腾飞。清波,也在慢慢成长。
她的哈哈打得特响。她的话音中,宁波方言偏重,里面也渗有少量的普通话。与她对话,有点吃力,即使她嘱你用本地方言,可你与她对话上路以后,再绕过那道普通话的“弯”,实在费劲。她见人,亲近又亲和,无拘又无束。不是兄妹,胜似兄妹。乡里同她工作的人,说她像只麻雀,成天唧唧喳喳,但又不厌烦这只“麻雀”,这只“麻雀”能驱赶孤独,带来喜悦。她的话,虽多,但重复语句极少;虽快,却有磁性,容易溶进人的灵魂,荡出笑容,牵出思考。乡里有的干部若哪天没有见到她,就像掉了一个什么东西似的,等她一回来,又像沸腾的水闹热起来。
她不会赌博,麻将认得来她,她不认识麻将。连抓鸟叫什么籽,她都一窍不通。她爱唱歌,有空,一个人都会哼出悠扬的一曲。她唱的歌,不仅仅是流行歌曲,桑植民歌她也会唱。听她唱歌,是享受,感觉舒服,那声音如同泉水发出的叮当,清亮。她唱的歌,字正腔圆。她不爱跳舞,其实跳舞也是一种享受。她不是不会跳,而是你与她跳舞,有压力,你往她面前一站,渺小自然出来:她,一米六九的身材,与一般人跳舞,她宛如带着一个小孩,感到一点也不协调。她的戏,演得特别,无论是小品,还是话剧,角色到位,形象逼真。笑的时候,立刻笑;哭的时候,猛地哭。她有赵本山的功夫,会自编、自导、自演一些节目。她演的戏,十有八九催人上进,但也笑得掉牙。
她,大学毕业跑来桑植当村官。桑植,很多红军打着绑腿从这里出发。这里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她住的村是苗寨。苗寨属廖家村镇管辖。这里苗族人多。村里说富裕也不富裕,反正,饭有吃的,衣有穿的,屋有住的,老百姓缺的就是一个字:“钱”!这个村,听起来遥远得很,其实就依偎在镇政府旁边。村支书的媳妇到浙江打过工。村支书无妹妹,称小龚为妹;小龚家无兄,喊村支书为哥,叫村支书的妻子自然就是嫂子。她们相互叫得亲热,喊得十分亲切。清波住在空气清新的村庄里,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她在村里,闲不住,不时策划着村里的未来。
清波到组织部跟过班,到县委办跟班,而今她成为一名副镇长。她这个人物在我的笔下是不具体的。不过,在我描写她的时候,想笑了,笑她说话幽默,笑她笑的时候雪白的牙给露了出来,还想起“清波池里拨清波”的那种意境。
佩文
几个朋友,同坐一趟车往乡下检查。突然,他们不约冒出同一个话题:“你怎么不写几笔佩文乡长?”我没有作声,因为,自己曾写过初识小郁,着笔黄河记忆,可没描绘久识的佩文妹?当晚,我趴在桌子上,就着朦胧的烛光,素描着佩文妹的轮廓。
佩文,两只眼睛有味。我说的有味,并不代表其眼鼓得有味,而是它如深山老林里的泉眼,潜藏着力量。你难捉透它的精灵。她不仅眼有魅力,一副苗条的身材在桑植的大街小巷或者田野村庄也为数不多。她走起路来,如风,浅浅的酒窝一绽,给你绝对有偶遇鲜花的感觉。她的步伐矫健有力,皮鞋点在地板上的声响,别人一辈子也难模仿。在县委实践办工作时候,她常常往县学习实践办走来上班,大家老远就知道是她来了。
虽没听过她的歌,但听人说“棒棒捶在岩头上”等桑植民歌,她哼唱得特爽。她能喝酒,但她从不张扬。喝酒,虽是一种享受,但喝多了也累。一般情况下她坚决不喝,连酒杯都不端。酒桌上,她遇上几句话的凑合,会自告奋勇地站出来,礼貌地走到你面前,举起透明的酒杯,亮出微笑敬你,你喝得得喝,喝不得也得喝。喝之中,她几句漂亮话往酒里一融,溶进你的心里,醉红脸的是您,可她若无其事。
与她一起工作是一种享受。她到县学习实践办前,还在“进门一背牛屎粪,出门一背马桑棍”的苦竹坪工作。百姓喜欢她,干部关心她。她,见你脸上泛愁云,会用贴肉的话驱赶;您收获喜悦,她会像添加剂一样给你注入更多的高兴。在乡里,她从不埋怨条件差,总默默无闻地工作。无论在哪里工作,她都肯谋事,肯做事,会做事,做好事。她做事,与时俱进常挂心头,只要一接受任务,谋划就开始,想方法,出主意,像绘图一样,思考圆满,做得漂亮;她做事,行动如箭,细字当头,从不粗手粗脚,总小心翼翼,就是写材料完稿以后,也得像青蛙捉害虫一样字斟句酌,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字词和标点;她做事不投犯规的球,领导怎么交代就怎么执行,就是别人说她办事不晓得绕弯,她也要按原则办;她做事,快得如她走路一样。快中,好字当头,质量领先。
佩文,钟姓。本科文化。今年不上三十。她,一个十分气质的女性,一张迷人的“画帖”。
阿波
阿波,满脸长着牢骚胡,但不牢骚。他的胡子,比长短,与贺龙的胡子可争上下;他的形象,去扮演贺龙,比彭天扮演毛泽东不会差。
阿波,年纪轻轻,一块茂密的胡须掩饰着他的实际年龄,如同一棵发芽不久的树,几把藤子一缠,就认为它老了。当然,老也有老的好,不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嘛。我想不虚伪地告诉你,他只是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多了七、八年在农村工作的经历。
初与他接触,显得比一般的陌生人陌生。这是个性的使然。人,如果没有个性,如同钢琴弹奏没有抑扬顿挫,好比散文没有节奏,谁也不爱听,谁也不愿读。认为他傲,其实,你稍微有点耐心,时间一长,便知他肚里如同宰相,心似大海,从不背面说人长,道人短,从不借井下石,砸人手脚,更多的是,他能把你从痛苦旋涡中往快乐的岸上扯。与他交道过的人,都有同感,认为这个胡子朋友值得交,可深交。
他把自己的心情看得重。有空,他就拖根钓杆,哼上小曲,沿公路,抄小道,去河边或湖边或鱼塘边,寻找那份宁静与安谧。他像一只鸭子,静静地呆在那里,等待钓杆上的浮子的滑动,就是一天到晚,浮子没有丝毫表示,他仍能收获一脸的笑容,收获脸肚的愉悦。无事了,他也喜欢品包谷烧,桑植是产这东西的地方。当然,其他的酒,他也喝。他喝酒,喝的是感情,喝的是心情,常一碰杯,别人还没说起醉,他的脸就跟灌了猪血一般。这些之外,他还喜欢打猎。他在乡下工作时,给他封了个什么“猎手”头衔。别人以为“猎手”就是守野猪的。后来,才弄清楚,他肯赶山,牵着一只黑得像煤炭狡猾如狐狸的狗,钻山。山里那些不属保护的动物,常倒在他的枪口之下。虽然他跟我一样近视,但把子够准。
乡下的日子,他过了几个春秋。那个地方,寂静得扎实,天一黑,鬼都打得死人。那地方,叫岩屋口。最出名的,是一条公路穿过岩屋的心脏。山里人见沱子大雨来,岩屋就成他们吹不倒、淋不坏的一把天然巨伞。在那里,他不是成天躲在岩屋里,而是在狂风扫、大雨洒之中,与风搏,同雨斗,搏出了精神,斗实了骨子。他下村入户,脚板上,泥巴裹满裤腿,脚上冒出一个又一个的泡儿。那干劲,如同百米冲刺一样,非争个第一不可。因此,他的工作常获乡里冠军。他,把激情燃烧在村庄,把毅力诠释在村庄,把果实挂满在村庄。
进城以后,他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从糠桶跳进米桶就万事大吉,可他热情如初,工作拼得命,当得饭吃,忙得团团转,就是头转昏,脚扯筋,嘴里还是那句“人生就要拼!”说起来,真有趣:有天晚上,他的办公室一片黑,以为里面无人。他一咳嗽,原来是他趴在那儿一个劲地赶着第二天需要的“货”,双手不停地敲击着那已经磨融的键盘。等他从办公室出来,大门早已关闭,如果不是那道喊声,他真的还要在办公室过夜。
我所说的阿波,刘姓也。他是一幅画,印在我的灵魂里,很久,如果再不轻描或者淡写,将会死去我身上的一些细胞。这里的献丑,仅作与他见面时的又一声招呼而己。
本文由 京廊文化根据互联网搜索查询后整理发布,旨在分享有价值的内容,本站为非营利性网站,不参与任何商业性质行为,文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部分文章如未署名作者来源请联系我们及时备注,感谢您的支持。
本文链接: /bangong/27309.html
